男女主角分别是灶王爷热门的其他类型小说《那年那月那一天那一刻全文》,由网络作家“黑五爷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小兵张嘎”四个字,枪管里还能塞纸炮。每次端起这把枪,我仿佛成了电影里的英雄,在巷子里和伙伴们“冲锋陷阵”。爷爷的烟斗是黄铜的,烟丝是他自己种的旱烟。烟斗壁上斑驳的弹痕,是他抗美援朝时修战地桥梁留下的纪念。有次我偷偷抽他的旱烟,被呛得眼泪直流,他非但没有责备,反而笑得前仰后合,说“烟味苦,日子才甜”。他的工具箱是檀木的,箱盖内侧贴着他手写的价目表:“做条板凳五毛钱,打张八仙桌两块五”。价目表边缘泛黄卷曲,却像他的人生般平整。最让我震撼的是爷爷的木工账本,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几十年的收支:1958年为生产队打粮仓,1963年给公社做黑板,1985年给孙子做木马……每一笔都工工整整,仿佛他的人生都浓缩在这些数字里。账本的最后一页夹着...
《那年那月那一天那一刻全文》精彩片段
小兵张嘎”四个字,枪管里还能塞纸炮。
每次端起这把枪,我仿佛成了电影里的英雄,在巷子里和伙伴们“冲锋陷阵”。
爷爷的烟斗是黄铜的,烟丝是他自己种的旱烟。
烟斗壁上斑驳的弹痕,是他抗美援朝时修战地桥梁留下的纪念。
有次我偷偷抽他的旱烟,被呛得眼泪直流,他非但没有责备,反而笑得前仰后合,说“烟味苦,日子才甜”。
他的工具箱是檀木的,箱盖内侧贴着他手写的价目表:“做条板凳五毛钱,打张八仙桌两块五”。
价目表边缘泛黄卷曲,却像他的人生般平整。
最让我震撼的是爷爷的木工账本,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几十年的收支:1958年为生产队打粮仓,1963年给公社做黑板,1985年给孙子做木马……每一笔都工工整整,仿佛他的人生都浓缩在这些数字里。
账本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照片,年轻的爷爷穿着军装站在木桥前,那座桥是他和战友们用生命筑起的。
桥下的河水在夕阳中泛着金光,他的身影挺拔如松,像一座永不坍塌的丰碑。
3 奶奶的四季厨房奶奶的围裙口袋里永远装着惊喜:春天有槐花蒸糕,夏天有冰镇酸梅汤,秋天有晒干的柿子饼,冬天有煨在灶膛里的红薯。
槐花蒸糕的制作过程最让我着迷,奶奶把槐花捋下来洗净,和玉米面、红糖拌在一起,上锅蒸的时候,整个灶屋都弥漫着槐花的清甜。
她纳鞋底的锥子“咔嗒咔嗒”响,鞋垫上绣的“平安”二字被针脚封得严严实实,仿佛能把平安锁进鞋底。
最难忘的是她做的“百家饭”——把邻居们给的米、面、豆子混在一起煮,说“吃百家饭的孩子好养活”。
饭锅里五谷的香气混着柴火味,在灶屋弥漫,连灶王爷画像都似乎被熏得笑眯眯的。
除夕守岁时,她总把压岁钱用红纸包好,偷偷塞进我枕下,钱币上的国徽在月光下泛着微光,仿佛能照见整个银河。
有次我贪玩把压岁钱弄丢了,奶奶非但没有责怪,反而从自己的布兜里掏出皱巴巴的零钱补给我,说“钱丢了可以再挣,心丢了就找不回来了”。
奶奶的灶台是砖砌的,锅底灰积了厚厚一层。
她总说锅底灰能治烫伤,有次我不小心碰翻热水壶
1 时光褶皱里的童年底色80年代的时光像一卷褪色的胶片,在记忆的暗房里逐渐显影。
巷口的供销社永远飘着红糖的甜腥气,玻璃柜台里整齐码放着“大前门”香烟和印着牡丹花的搪瓷杯。
买肉要凭票,买糖要排队,但父亲每月工资70元能换回半斤猪肉时,母亲总把肉切成细丝,掺着白菜炖一锅。
汤里的油星在搪瓷碗上晃悠,连喝三碗都嫌不够。
碗底沉淀的肉渣,母亲会捞出来拌进我的饭里,说“孩子长身体,得多吃点油水”。
那时的家是一间15平米的砖房,墙皮剥落处露出红砖的肌理。
冬夜,父亲在煤炉上烤红薯,火星子“噼啪”炸响,火星溅到地上,他便用铁钳子轻轻拨开,生怕烫着我赤脚踩上去。
母亲用缝纫机赶制厂里接的零活,针脚在棉布上踩出细密的节奏,缝纫机头的油渍在灯下泛着微光。
我和弟弟缩在床角听收音机,半导体里传来评书《岳飞传》,讲到“精忠报国”时,父亲突然放下烤红薯的钳子,郑重地对我们说:“做人就得像岳飞,脊梁骨得直。”
炉膛里的火光映在他脸上,汗珠在额角闪烁,像一颗颗小小的星辰。
窗棂上结着冰花,北风裹挟着远处工厂的汽笛声呼啸而过,但屋内暖黄的灯光把这一切喧嚣都隔绝在外,仿佛时间在此凝固成琥珀。
供销社的柜台后,总站着一位驼背的老伯,他的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。
每次母亲带我去买盐碱,他都会从柜台底下摸出两颗水果糖塞给我,糖纸在阳光下透出彩虹般的颜色。
有次我偷摸他抽屉里的糖,被他逮个正着,他非但没有生气,反而笑着说我“鬼精鬼精的”,从此每次都会多给我一颗糖。
这个秘密成了我和他之间的默契,直到供销社改制,他退休那天,柜台里只剩下一堆空荡荡的玻璃罐。
2 爷爷奶奶:旧时光里的守望者爷爷的木匠世界爷爷的木匠铺在院东角,刨花堆成小山,墨斗线在木料上拉出笔直的轨迹。
他总说“木匠活讲究个‘稳’字,人生也一样”,边说边用粗糙的手指教我辨认榫卯结构。
榫头与卯眼严丝合缝的“咔嗒”声,像在演奏一首古老的木工之歌。
最难忘的是他为我打的小木枪,枪柄刻着“
,她迅速抓起锅底灰敷在我手上,果然没起水泡。
灶台上常年摆着两个陶罐,一个装盐,一个装碱,揭开盖子时,盐粒在阳光下像碎钻般闪烁,碱面则像积雪般蓬松。
她舀盐碱的动作极轻,生怕洒出一粒,仿佛那些都是金豆子。
4 父母:在柴米油盐里编织温暖父亲的“粉笔灰哲学”父亲是中学数学老师,衬衫袖口总沾着粉笔灰,批改作业时红笔圈出的“√”像一枚枚勋章。
他总把教案本撕下一页给我当草稿纸,说“纸要写得满,脑子才装得满”。
有次我考试失利,他带我去麦田边,指着随风起伏的麦浪说:“你看,风把麦子压弯了腰,麦子没折断,反而长得更壮实。”
月光下的麦田像一片金色的海,他的话随着晚风飘进我心里,生根发芽。
<父亲的书架是家里最珍贵的地方,泛黄的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整齐排列,他每晚伏案备课的身影,是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剪影。
高考前夜,他骑自行车驮我去县城,车铃铛“叮铃铃”响了一路,车筐里温着的鸡蛋在颠簸中碎了一个,他掏出皱巴巴的手帕包住,说“碎了更好,补脑子更入味”。
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像两条永不分离的线。
车后座上的我,能闻到父亲衬衫上淡淡的粉笔灰味道,那味道里藏着他对生活的倔强与温柔。
父亲批改作业时,总用红笔在错题旁画个小圆圈,旁边写“再想想”。
有次我故意把作业本藏起来,看他着急的样子,他却笑着说:“小狐狸尾巴露出来啦!”
然后从抽屉里变戏法似的掏出我的作业本。
原来他早就猜到了我的把戏,却故意配合我演这场“捉迷藏”。
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父爱如山,却也能化作春风细雨。
5 母亲的“纺织厂时光”母亲在纺织厂三班倒,白班时她总把食堂发的午餐——一个窝头、一勺咸菜——分给我一半,自己啃着剩下的窝头,说“小孩长身体,多吃点”。
夜班回家,她裹着沾满棉絮的蓝工装,从兜里掏出温热的糖炒栗子,栗子壳上还留着体温的余温。
有次厂里发奖金,她买回一匹的确良布料,给我做了一件白衬衫,衬衫领口用红线绣了我的名字,穿上它去学校,连风都
,能捉害虫。”
然后举着木枪说:“它们是青蛙部队的侦察兵!”
我们立刻破涕为笑。
冬天堆雪人,哥哥用胡萝卜做鼻子,妹妹偷拔她的红头绳当围巾,雪人脸上歪歪扭扭画着妹妹的名字。
最疯狂的是玩“地道战”,我们在后院挖地道,结果挖到邻居家的鸡窝,被愤怒的邻居追着跑,哥哥护着我摔进泥沟,我俩在泥水里笑得直打滚。
哥哥是家里的“探险家”。
他带着我翻墙去铁路边捡煤渣,在废弃的厂房里玩“捉鬼游戏”,甚至爬上屋顶看流星雨。
记得有次他教我骑自行车,我在斜坡上摔得膝盖流血,他一边给我涂紫药水一边说:“疼就哭出来,男子汉流血不流泪。”
他的话和药水的刺痛一起,烙进了记忆深处。
有次他捡回一只受伤的鸽子,我们给它包扎伤口,放在爷爷的工具箱里养。
鸽子痊愈后飞走了,哥哥望着天空说:“它要去找妈妈了。”
那一刻,他眼里的光芒比鸽子翅膀还亮。
妹妹是家里的“开心果”。
她总能把爷爷讲的抗战故事改编成童话,把奶奶的百家饭说成“神仙粥”。
有次她偷穿奶奶的红绸缎嫁衣,在院子里转圈,裙摆扫起一地槐花瓣,像一只误入人间的红蝴蝶。
我们笑她“像新娘子”,她却一本正经地说:“等我长大了,要嫁给解放军叔叔!”
8 矛盾与和解为争抢最后一勺糖,我和弟弟把搪瓷碗摔在地上,糖溅得到处都是。
母亲没责备,只默默缝补碗上的裂缝,裂缝像一条银色的蜈蚣爬在碗沿。
后来弟弟用攒的零花钱买了块糖赔给我,我们躲在草垛后分着吃,甜得眯起了眼。
高中时哥哥考上县城中学,临行前夜,他把我叫到天井,把珍藏的《水浒传》塞给我,说“男子汉要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。
月光下,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像一柄出鞘的剑,也像一棵即将远行的树。
妹妹的“恶作剧”总让我哭笑不得。
有次她把我的作业本藏进鸡窝,害我被老师批评,但当她举着沾满鸡毛的本子嬉皮笑脸道歉时,我又气又笑,只能原谅她。
如今回想起来,那些争吵与欢笑,都是童年最珍贵的礼物。
9 秘密基地的童话后院的葡萄架下,是我们藏秘密的地方。
妹妹用碎花布缝的
带着骄傲的味道。
纺织厂的轰鸣声是母亲生活的底色。
她总说“三班倒的日子像陀螺,转得人晕头转向”,但每月领工资时,她数钱的手指却格外欢快。
记得有次她值夜班,我偷偷溜进车间看她工作,巨大的纺纱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,她站在机器前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,飞梭的棉絮在灯光下织就一片银色的云。
她的蓝工装被汗水浸透,贴在背上,却像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。
母亲的手掌上有厚厚的茧子,那是常年与缝纫机打交道的印记。
有次我发烧,她彻夜未眠,一边用湿毛巾给我降温,一边在缝纫机上赶制厂里的零活。
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身上,她低头缝纫的身影,像一尊用母爱浇筑的雕塑。
6 属于我们的“家庭会议”买电视那夜,父亲把存折摊在八仙桌上,母亲的手指在数字上轻轻划过:“这个月多买了肉,下个月得少吃两顿。”
最终全家决定买下那台熊猫牌黑白电视,安装时父亲爬上窗台架天线,母亲在屋里摆弄旋钮,我和弟弟趴在电视机前,雪花点闪了半小时,终于出现《西游记》的画面。
唐僧骑白马走过的沙漠,在15平米的屋里掀起一场视觉风暴。
电视成了家里最珍贵的宝物。
每天傍晚,邻居们端着饭碗挤在屋里,屏幕上的光影在每个人脸上流转。
最难忘的是看《霍元甲》,父亲跟着主题曲哼唱,母亲在缝纫机旁踩着节奏,弟弟把爷爷的木枪当“迷踪拳”,在屋里舞得虎虎生风。
那台老电视最终在某个暴雨夜罢工,父亲拆开电视机检修,满屋都是电路板烧焦的味道,但再也没能修好。
家庭会议总是充满烟火气。
记得有次讨论是否要养一只小狗,我和弟弟拼命点头,父亲却担心影响学习,母亲则说“小狗能看家”。
最终父亲妥协,但提出条件:“每天放学必须写完作业才能喂狗。”
小狗进家门那天,全家像迎接新成员般热闹,弟弟甚至把自己的红领巾系在狗脖子上,惹得全家人哈哈大笑。
7 兄弟姐妹:吵吵闹闹的成长交响曲游戏里的江湖夏天在河滩捉蝌蚪,我和哥哥比赛谁养的青蛙先叫,结果蝌蚪全变成癞蛤蟆,吓得妹妹哭了一晚上。
哥哥却安慰她:“癞蛤蟆是益虫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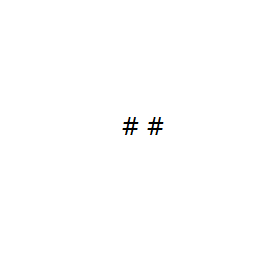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